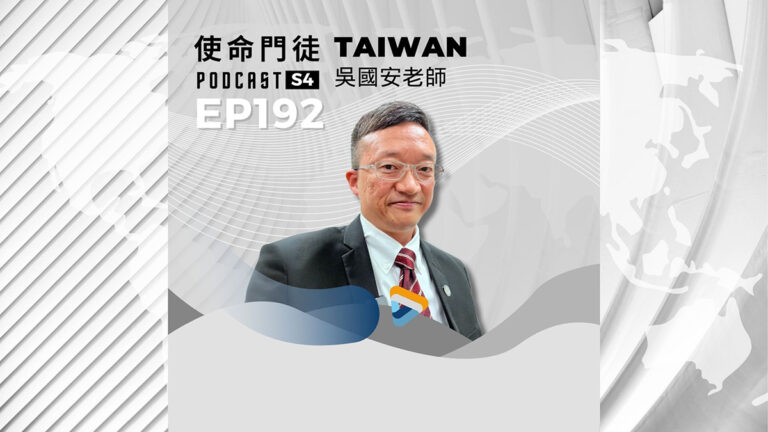作者:張俊明牧師(馬來西亞神學院(STM)學生事務主任)
引言
馬來西亞(簡稱:馬國)是一個多族群、多宗教的國家。主流族群的當權者(巫統)建構了「馬來人至上」的政治論述,強化了族群差異和對立,將其他族群視為威脅和外來者。這一論述為種族主義政策鋪路,對國家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導致族群分離和非馬來人國家認同薄弱。
本文探討教會在馬來霸權和族群分離中的回應。為了共善,需要抗爭。抗爭物件是種族主義政客,而非其他族群,目標是啟動底層族群的友誼聯結,達成共融願景。
馬國政治處境的鳥瞰圖
馬來西亞的多元族群社會結構可追溯到英國殖民時期。為開發資源和促進生產,英殖民者從中國和印度大量引入勞工,形成多族群共存局面。1957年獨立時,各族群權力分配成為關鍵議題。經濟弱勢的馬來族群擔心被邊緣化,要求在獨立憲法中保障其權益,最終憲法賦予馬來族群及其宗教(伊斯蘭)特殊地位。
馬國憲法因此成為一種奇異的組合:一方面,憲法包含自由民主的理想,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又強調馬來人和伊斯蘭的特殊地位,帶有種族性優惠待遇(人人平等?)「馬來人至上」的政治論述正是在這種憲法基礎上被過度解釋的結果。例如:經濟弱勢的「特殊地位」優惠被發展為「馬來人特權」的論述,從原本有時限的經濟優惠演變為因族群身分而享有的永不可剝奪的特權。
這種論述得以背書後,隨即推出了一系列強制性優惠馬來族群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y Policy,NEP),這項政策自1970年「513族群暴動事件」後實施。由於優惠政策一波接一波不斷推出,馬國人戲稱NEP 似乎成了「永無結束的政策」(Never Ending Policy)。政府將這些政策稱為消除貧困的扶弱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旨在平衡族群間的貧富差距,實現族群和諧。
馬國社會的挑戰
1. 種族主義的不公
雖然扶弱政策有其必要性,但問題在於:所有馬來人都貧困嗎?印度人和西馬的原住民(Orang Asli)是否也需要幫助?為何這些群體未被納入扶助對象?新經濟政策(NEP)中存在種族主義傾向。
此外,NEP的受惠者多為上層馬來權貴,而非貧窮的馬來族群。NEP的初衷是消除貧窮,卻已演變為馬來權貴致富的途徑。
2. 族群分離
另一個挑戰是族群分離。首先,這種分割源於殖民地時期的歷史遺留。東南亞問題專家J.S. Furnivall指出,20世紀東南亞殖民統治時期,各族互動僅限於市場或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沒有互動。1其次,獨立後馬來人至上的政治論述加劇了這種分割,將國民區隔為「馬來人」和「非馬來人」。作為馬來西亞的基督徒,我們有責任發聲,努力逆轉族群區隔的現狀。這是馬來西亞公共神學需要思考的重要議題。
問題梳理與分析
在回應問題之前,需要釐清問題的癥結。我們需要問:造成這困局的根源在哪裡?或者說「敵人」是誰?
1. 族群或階級分析視角
族群視角(Ethnic Perspective):當權者總是以族群視角來分析問題,常將問題歸咎於其他族群。例如: 認為馬來族群受到華人和印度人的剝削,或認為華人和印度人作為外來者,奪取原屬土著的資源。
階級視角(Class Perspective):不可忽視以階級視角來看待問題,這種視角認為困局背後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益者是馬來政治精英,而非其他族群。
2. 族群視角的弊端
造成族群分離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差異族群,而是種族主義政客。他們通過極端言論成為挑戰其他族群的英雄,製造族群對立和分離。我們不可忽視「躲在細節中的魔鬼」。我們需要意識到,發洩對政客極端言論的不滿在生活中的馬來族群身上,是中了魔鬼的詭計。相反,我們應採取階級性的抗爭,聯結各族群,對抗分裂族群的思維和合法搶奪公共財富的政客。為此,下面將提出一種日常抗爭,作為教會回應馬國族群議題的建議。
作為日常抗爭公共神學的思考
為了應對馬來西亞的族群問題,我們提出一種「日常抗爭公共神學」。這種神學通過日常生活中的抗爭,促進族群共融。
1. 關於「抗爭」
我們的抗爭是為了公共利益,尤其是為弱勢群體而戰。如果馬來人是最大的貧困群體,我們就為他們抗爭。目標不是革命或抵制不同族群,而是實現正義的共善和族群共融。
什麼叫日常抗爭,先借用Michel de Certeau的「戰術」抗爭理論來說明:2
★策略(Strategies):強者(如政府、企業)用來控制空間的方法,涉及長遠計畫和系統安排。
★戰術(Tactics):弱者通過靈活、臨時的方法在強者設定的框架內進行抗爭,依賴即興和機會主義。
「日常生活中的抗爭」即戰術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各種細節中,如語言的使用、空間的佔用、時間的安排等。這種抗爭方式並不直接挑戰現有權力結構,而是在被異化的族群關係中(馬來人 vs 非馬來人,神聖 vs 世俗化等),透過日常分享、相遇和友誼的建立,重新理解其他族群,作出不同的國族想像,並領受抵制上層掌控的能力。
在馬來西亞的族群問題中,戰術抗爭提供了微觀層面的抵抗方法。通過跨族群的日常互動,個體可以逐步削弱種族主義政策的影響,推進族群共融的目標 —— 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人的「國族」認同。
2. 共融的神學理解
(1) 互為主體性與他者優先性:
共融要求各族群建立互為主體的關係,尊重彼此的自主性。馬丁.布伯在《我與你》中提出的「我 —— 你」關係,強調直接、真誠和尊重的互動。3這在基督教中體現了上帝與人之間的關係,要求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對他者的接納與尊重。
(2) 共融的心志與經驗:
共融不是通過達成統一共識實現的,而是一種願意不斷學習和溝通的心志。共融的前提是對差異的尊重,體現了謙卑和去自我中心的見證,也是一種靈性的操練。
結語
從馬來西亞公共神學的經驗中,我們可以提出普世宣教的新視野:
★教會需要作為種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的批判者,揭露和反對種族主義政策。
★在族群分離的社會中,基督徒應成為促進共融的力量,致力於建立跨族群的友誼和理解。
即使作為少數的基督徒無法直接參與上層的政治改革,但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友誼聯結,仍能見證上帝國的事業。我們認為,底層廣大的公共領域才是更為實質的公共領域,見證上帝國的行動即是一種宣教的新視野。
本文刊載於《今日華人教會》2025年刊,第三十三頁至三十六頁。
文字編輯:呂昀嬪姐妹
註:
- 1.J. S. Furnival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304. ↩︎
- 2.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pp 35-36. 塞托(Michel de Certeau),《日常生活實踐:1. 實踐的藝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
- 3.馬丁布伯(Martin Buber),《我與你》(上海:三聯書店,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