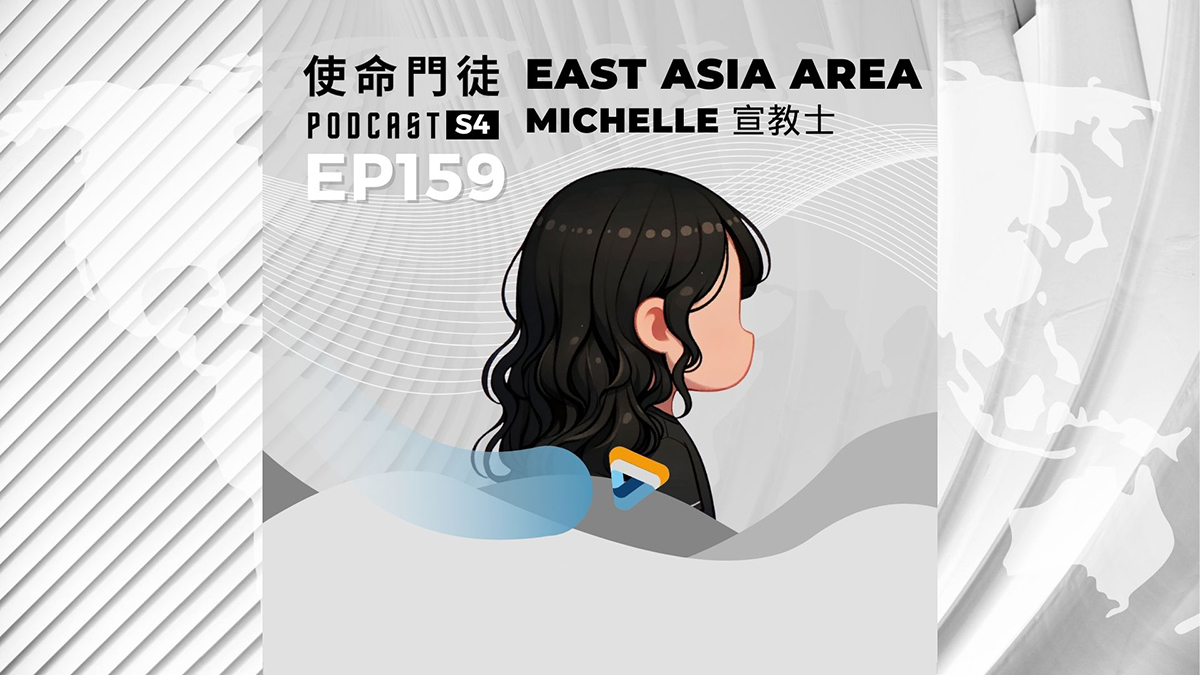
EP159 OM世界福音動員會Michelle 宣教士:如何開啟「整全宣教」的多元性?要怎麼從「民族中心主義」中得釋放?
嘉賓:Michelle 宣教士(OM世界福音動員會)
主持:董家驊牧師
打開視野回應呼召,開啟福音歷程
董:自1974年第一屆洛桑福音大會以來,全球的福音派教會產生了一股新的動力,投入普世宣教,也催生出華福運動,如今五十年過去了,這五十年當中發生了哪些改變呢?又有哪些宣教上值得我們反思?今天我們邀請到宣教機構——OM的年輕同工Michelle來和我們分享,近年普世宣教的趨勢和普世教會在反思的議題,以及我們在關於宣教既有的思維上存在哪些盲點和更新的機會。
首先,可不可以請你很簡單的介紹一下你自己,很多人可能第一次聽到你的聲音,也很好奇你的人生經歷了什麼?你怎麼樣回應宣教呼召跟這一路的旅程跟故事。
Michelle:我是台灣的高雄人,從小在教會長大,我是第五代基督徒,在家中的長輩有人是牧者,所以是在牧家的家庭長大的。我第一次參與宣教是在升高中的暑假,跟我們教會的學生牧區一起到緬甸短宣,我還記得那時候緬甸在大馬路的十字路口,都還是有拿著機關槍的士兵去站崗的。後來我在忠僕號過十八歲的生日,那時也是一個短宣,忠僕號就是福音船屬於我現在服事的機構,是我們一百多個事工裡面其中一個事工。二十歲的時候才全職呼召做宣教的服事。
我大學畢業之後,我到美國的Fuller學院讀跨文化研究的碩士班,我那時候的副修是危機中的兒童,就是說怎麼服事在戰爭線、怎麼服事貧窮線、怎麼樣服事在危機當中的兒童們,這是我在Fuller神學院的副修。我在美國畢業之後,又在一些不同的國際的NGO工作,比如說世界展望會的國際總部,我在他們的策略部實習,然後在他們的國際招募部裡面,服務了大概三年多,然後神才呼召我,2022年開始回來亞洲,加入OM這個東亞區的團隊,在他們的訓練部門裡面,做宣教士培力方面的服事。
董:你剛剛說到你在緬甸短宣的時候,在忠僕號過你十八歲的生日,所以你是高中畢業就上船嗎?
Michelle:對,我就是升大學的時候,那個暑假上船的,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是考學測的時間,船剛好來台灣,所以我就寫信給彭書睿哥,然後他就說可以當船的先遣部隊的志工,於是就一邊準備我的學測,一邊去船上的先遣部隊幫助他們。
回想我自己被動員的過程當中,我覺得是高一的時候忠僕號來台灣,當時我在參加我們學校的團契,他們有一個十九歲的日本宣教士到我們的團契分享,我覺得很感動,怎麼會有一個這麼年輕的亞洲女生,特別在升學主義志向的環境長大的人,願意放下自己生命當中最精華兩年的時間,十八、十九歲上船服事神,所以那時候覺得很感動。回過頭來我才發現原來我被動員,竟然是被一個日本的宣教士感動,我們也都知道日本是福音很危急之地,我居然是被一個這樣子背景的宣教士感動、被他動員,我到現在還沒有機會親自跟他說謝謝,但我蠻感謝神的,讓我因著這特別的方式被動員去做宣教。
董:所以你二十歲的時候就有一個全職的呼召在宣教上,大學畢業後就到了Fuller神學院讀書,你讀的專業也很有意思,是跨文化(Intercultural study)宣教學院和副修危機中的兒童,這個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你是在學什麼?
Michelle:我們那時候學的有幾個方面,第一個是「Child protection」:你要怎麼樣保護兒童,特別是在宣教的方面,或者是你在服事的過程當中怎麼樣保護兒童;第二是「Child empowerment」:怎麼樣在你服事宣教的過程當中,或是在你的兒童主日學這些設計當中,怎麼樣去培育孩子,因為孩子他們也是有能力的;第三個是「Child participation」:就是我們相信孩子,不論是在宣教中或是在參與神國的事工當中,他們都是神國的一員,他們不是被動的解鎖者,他們是可以很主動地參與在神國的事工當中的參與者。所以這是三個我們學的部分,特別是針對戰爭線或是愛滋病或是在貧窮線下面的孩子們怎麼去培力他們,這是主要學的部分,這算是我在Fuller神學院的副修,因為那時候Fuller有不同種的副修可以選修,有植堂、有國際發展,也有所謂的伊斯蘭的研究。
兒童在宣教中扮演的角色
董:你那時候為什麼會選這個副修?因為其他的好像聽起來比較像是一般會去讀跨文化學院會去修的,你怎麼會選這個副修?
Michelle:其實我在從一開始十五歲到緬甸短宣的時候,我就對孩子們還蠻有負擔的,我十九歲又回到了柬埔寨,就是十八歲跟船到柬埔寨,十九歲又跟著大學的志工隊到柬埔寨的時候,我就發現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Child participation」,就是一個三歲的柬埔寨的孩子,他在跟我玩的時候,他就很想要教我怎麼樣講柬埔寨文的一二三,在那之後我感受到原來小孩子是有能力去協助我們的,身為一個在宣教被呼召要服事的人,我們要怎麼樣服事孩子們,怎麼樣跟孩子們參與在宣教的事工,我就對這些事情很有興趣,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到底要讀哪一間神學院去裝備,剛好看到Fuller就有這個「Intercultural study」的課程,是三合一,有神學有宣教學也有這個副修叫「Children at Risk」,所以我就選了。
董:雖然今天我們主要聊的不是這個主題,但我剛剛聽到說還蠻感動的,就是一般想到危機中的孩童大概只是第一層:如何保護,可是你們談的不單單只是保護也是賦予他們權利(Empower),「Participation」就是孩子也是可以參與的,孩子不只是我們一般常想孩子的時候,都是他們是教會的未來, 宣教的未來,我們常常忘記一件事情是,上帝把他們放在這個時代,他們也是教會的現在,宣教的現在。
Michelle:謝謝董牧師,而且我還記得你在Asia 2020的時候也有講說,我的Now Generation不只是年輕人,或是所謂中生代或是上一代的人,其實Now Generation也包含所謂我們現在已經出生的零到十八歲,他們也是我們的Now Generation。
反轉對宣教既定框架的想像
董:從你分享的經歷,除了在台灣讀書也去到了Fuller讀書,後來又到了北美的世界展望會去服事,然後又回到台灣的OM,其實在整個塑造預備回應呼召的過程當中,包含你到Fuller去讀書應該是帶了一些期待,就像你剛剛講的你會選這個神學院是因為你看到它的一些課程,Fuller應該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早有所謂的宣教學(School of Mission),現在改名叫School of Intercultural Study(跨文化研究)的學校,我很好奇你在進這個學校前你有什麼樣的期待,以及你進到這個學校真的讀書的時候,你有什麼樣的收穫或者是期待中的收穫?或是意外的收穫?
Michelle:我那時候剛開始要去讀Fuller的時候,其實只是很單純覺得說我在服事之前,如果能夠接受一些專業知識的裝備、神學的認識跟進深,對未來宣教服事可能會有幫助。我那時候期待我自己說,我畢業之後就會到一個國家的某一個地方去服事他們的小孩子,這是我進去Fuller對我自己的期待。我覺得神很特別,當你期待這樣的時候,神的計畫總是大過我們的想法。後來我被神整個轉變,是在我去東南亞的某一個地方山竹國實習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好像不論是在宣教機構裡面,或是在基督教的非營利組織,像是世界展望會這樣子的非營利組織,其實人資也是很重要,比如說選訓留用方面,如果在這五個方面裡,一些機構裡面的配套措施或是機制不夠完善的話,其實很容易造成宣教士的流失,或是宣教士的崩耗,或是招募的時候沒有過濾掉一些比較不適合的人,我就在那次在因為宣教,因為要畢業實習的時候,發現了人事對於宣教的重要性。
後來神很奇妙,祂就帶我到世界展望會,在他們國際總部的人資部裡的帳務部去學習。我就看見,原來所謂我們都會覺得好像人資是第二線後勤,但是其實如果沒有這一些的人願意地去服事跟擺上,一個機構是很難有一個完善的體制或是系統(system) ,可以讓宣教士很放心地去第一線服事。這也是打破我自己的觀念,就是說原來神的宣教事工這麼大,神的宣教不是那個出去的人才叫做宣教士,我自己被神打破我對宣教的框架。
董:所以有點像你的期待被轉了一個彎,你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好像去到那邊的人,可是上帝也讓你看到,整個後勤團隊培育人才的保護、篩選、支援的重要性。
Michelle:對,特別是在世界展望會,我自己在招募部,看見更多在宣教上面的一些可能會有的誤區等等,當時我就在想,華人說要參與宣教的時候,是不是有一些誤區,或是過去一些西方國家,甚至是韓國他們已經做好的所謂最佳作業流程(best practices) ,或是他們犯過的錯誤,有沒有什麼是我們能夠避免的,這個是我在Fuller也看見的,在世界展望會也親身經歷到培訓宣教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個培訓不只是說他們出去之前給他們培訓,而是在他們在呼召,或是已經回應呼召的過程當中,他們能夠持續地接受所需要的訓練,以至他們能夠更貼切地在神呼召之處服事。
對宣教士認知的誤區
董:那我很好奇,像我們一般講到,怎麼樣選拔培育支持宣教士的確很重要,那你覺得不論是教會或者是一般的基督徒,我們在想宣教士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常常存在的誤區有哪一些?或者是我們現在的做法當中,有哪一些我們可以從其他國家的機構組織的經驗當中少走一點冤枉路?
Michelle:有一個誤區是,好像宣教只有單選題,就是好像回應宣教的路只有一個方式,我們選擇宣教士的方式也只有一個方式,但以我目前在我自己機構跟其他機構互動當中,我看見其實所謂的宣教是很大的,我舉個例來說,在我自己的機構裡面我們有做運動的事工,有做藝術的事工,我發現,如果我們用傳統的宣教框架來招募,再遴選或者是在培育宣教士的話,這兩種人很快就會被篩掉,因為他們不在傳統的宣教士範疇中,所謂你要去到某一個地方偏遠的地方,就是未得之民(UPG)的地方,然後去那邊就是以傳福音為主的宣教,可是其實神的宣教很大,當我們覺得宣教是單選題的時候,我們其實會遺漏掉看見到神的作為。如果說上帝使命(Missio Dei)是一個大桌子,那桌子上有很多物件,神在祂的宣教當中放了很多物件的時候,我們其實可以看見很多在桌上的東西,而不是只看見桌上的馬克杯。那我覺得這可能是我發現在宣教上面會有的誤區。
什麼是上帝使命(Missio Dei)?它對宣教的意義是什麼?
董:你可不可以在整個宣教學的討論中再更多解釋一下上帝使命(Missio Dei),其實Fuller神學院算是很早就開始關注宣教,在過去五十年當中全球的宣教論述,包括洛桑福音運動,都跟Fuller神學院早期的一些老師和現在的老師都有息息相關,當然在這五十年當中也有一些改變,也有一些發展,其中上帝使命強調宣教首先是關於上帝的宣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但是可能一般人聽到這個上帝使命(Missio Dei)的時候,會覺得這是哪一國的文字,英文其實翻譯就是「Mission of God」或者是「God’s Mission」——上帝的宣教,那這個概念是什麼以及它對於我們對宣教的理解跟實踐,又帶來什麼樣的挑戰更新或影響呢?
Michelle:我試著用很簡單的方式,而不是很神學或是宣教學的論述來談,我覺得上帝使命(Missio Dei)其實就是神對祂受造世界的人事物的一個很大的心意,祂希望人跟祂和好;祂希望人跟人之間和好;祂希望人跟祂的受造物之間和好,在這一整個很大的範圍裡面,都是神的心意,都是神的宣教。整個上帝使命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回到神的心意當中,回復到祂所創造我們的那樣子的心意裡面。也因為有這個上帝使命的概念,你怎麼樣回應神對你的心意,你怎麼樣回應神對受造世界的心意,每個人都不同的,神對每個人的呼召都是不太一樣的。
也因此在回應神的宣教當中,就不再只有所謂的「敲門傳福音」(door to door)的樣子才叫做宣教,我們才會發現,原來宣教也是當你陪一個弱勢的人們走一段路;或者是說你看見世界不公義的時候,你為這些人這些事物發聲;或是你去關懷神所造的這些環境,其實都是回復到神最初創造我們,祂想要與我們的關係合一的使命。所以我會覺得上帝使命比較是這樣子大方向的概念,最終也是希望萬族萬國萬民萬邦能夠認識主,因為那個也是神創造的心意,所以並不是說「door to door」的這種傳福音就不再是神的宣教,而是的確它就是神的宣教的其中一環,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董:這樣聽起來整個上帝使命在上帝的宣教中會帶出我們今天常常在強調的所謂整全的宣教,你可不可以也跟我們介紹一下,整全的宣教是什麼意思?
Michelle:一開始我們當然就是希望人家可以信主,信耶穌得永生,這當然是宣教當中很重要的一環,過去整個西方在宣教的發展當中,你會發現我們的確是需要去傳福音,但是在傳福音的同時,我沒看見人們的受苦,我沒看見人們的需要,那怎麼樣用比較全面性地去回應人的需要,以至於他的生命是從裡到外的被轉化,因為當一個人他的確信耶穌了,他有永生的盼望,可是他就是每天餓肚子,可是他就是每天還是遭受逼迫,那這樣子我們還是失去了神把我們造為人,並在這世界可以享受神受造的心意中,好像就是我們就剝奪了他們在世上的時候這樣子的一個權利。我覺得整全宣教比較像是說,我們接受福音是很重要,但是我們與人的關係的恢復,與受造之物的關係的恢復,與神關係的恢復都是很重要的,是全面性的。
董:你剛才這樣講的時候讓我想到Christopher Wright是一個很重要的神學宣教學家,他在一本書叫《宣教中的上帝》裡面,他特別提到整全宣教跟佈道的關係,你剛才的分享也讓我想到他講的這段話,他說與其說佈道是整全宣教的首要工作,不如說是終極性工作,什麼意思呢?他說宣教不一定從佈道開始,它可以從人的生理的需要、心理的需要、屬靈和社會需要任何一點來切入,但最終若未包含宣告上帝的話語、以基督的名悔改的呼籲、信心和順服的生活,就仍未完成任務,是有缺陷的宣教,而非整全的宣教,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談的話,其實整全的宣教並不是在否定傳統的宣教,事實上反而是更加地肯定,最終呼籲人信主作主門徒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是我們在切入去關懷的時候,上帝的心意是比這個更大的,比我們加入一間教會參加聚會更大的,上帝的心意是要恢復不單單是我們與祂的關係,也是我們與彼此的關係,也是我們與受造萬物的關係, 這樣理解跟你剛才講的你覺得是呼應的嗎?
Michelle:我覺得是,而且因為我自己經歷過在不同的基督教的非營利組織裡面工作,我其實可以很清楚的,甚至第一線的體會到說,當我們在做所謂的扶貧濟弱,或是說我們在服務人的需要的時候,若是最終沒有福音在我們的心裡,或是沒有這樣子的心願,在當我們在服事別人的時候,其實真的是會覺得少了什麼,這也是為什麼我目前覺得神呼召我回來,是在宣教的機構裡面服事,而不是繼續在非宣教機構裡面服事。
宣教不應該只是單一選項
董:那我也很好奇當你跟身旁的朋友分享,你是透過這個方式在回應宣教呼召的時候,有沒有被挑戰過,或被這樣問過:第一個是宣教不是都是應該要去第一線嗎?我知道你剛才有回答過,但是你有沒有被人這樣問過;以及第二個是搞藝術、搞運動這樣也算宣教嗎?那宣教會不會太廣?是不是什麼都可以算宣教,你有沒有被這樣挑戰過?如果有的話你會怎麼回應這樣的疑問,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他是發自內心很誠實地把他心中的疑問提出來,那你會怎麼回應?
Michelle:我很常被問啊!這就讓我回想到,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宣教的定義,這也是為什麼我慢慢地去理解到,宣教不是單選題,好像說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其實應該是多選題,怎麼說呢?我回應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我不是去第一線,我曾經跟人家回答,我覺得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我其實是美國教會差派回來亞洲宣教的,所以對於我美國的差派教會,我已經是在第一線宣教,因為我人在亞洲,所以我覺得所謂的第一線其實也是相對的,但是最終的是,我們有沒有回應神放在我們心中的呼召。
還有就是方式,你現在可能是用訓練,或者是用人資或是甚至有些人是藝術或運動,這就回應到,今年(2024)九月份第四屆洛桑大會要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叫做「Polycentric Mission」,也就是「多中心化宣教」,多中心宣教的概括就是:「From everyone to everywhere with many centers」(從各民到各地),當神給你一個呼召的時候,其實我們都可以去跟神求問說,我們要怎麼樣去回應神的呼召跟世界的需要,並不是只有某一個方式。
我十歲的時候讀《深入非洲三萬里:李文斯頓傳》,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宣教是怎樣,他就在那邊跟河馬打架啊,跟鱷魚戰鬥啊等等的,這是我知道的宣教,但是他同時也是用醫療去傳福音,然後同時也去停止黑奴的販賣。那在台灣我們有馬偕醫生,他也是透著行醫去做宣教,所以其實我們參與神的宣教有很多的方式,並不是只有直接的傳福音這樣子的方式才是宣教。
董:你剛才講第一線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然後談到今天的宣教是全球是一個多中心的宣教,我其實很有感觸,因為我今年(2024)四月的時候在中南美服事,那中南美我們一般想到就是天主教國家,廣義來講也算是基督教國家,而基督新教在他們當中也是很活躍的,可是中南美大部分的國家華人基督徒的比例不到1%是0.1%左右的,所以按照今天的標準來講,其實這個群體,幾乎就是未得之民的比例。我這次在阿根廷就遇到有一批韓國的宣教士,他們現在在考察,是不是其實應該要投入中南美的華人的宣教佈道的工作裡面。
我覺得這就是你剛才講的很多東西真的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就是說對中南美的國家基督徒比例是很高的,可是如果以華人這個群體基督徒的比例卻不到1%,那你說他們需不需要宣教士,所以就看你是從哪個角度來看。只是好像很多時候我們耗費了很多的力氣,努力地要去做一個定義,討論一個定義性的問題,當然定義很重要,因為有定義我們才能討論事情,但是在我們的思維裡面,談論這些定義或選擇的時候,都是一種單選題的考慮,好像比較難接受「兩者皆是」,或者其實對的選項不一定只有一個。
我想也許不單單是指這個宣教的圈子,包括整體華人的社會,或者是整個教會的文化,你覺得為什麼我們比較習慣的是單選題,而單選題的思維又有哪一些的限制呢?
Michelle:我在讀Fuller的時候,也是必須要面對這件事情,特別是當我在面對一些不同神學主義跟宣教學的闡述的時候,因為我是在華人的文化脈絡中長大,畢竟在台灣土生土長以考試為主長大,那考試就一定有標準答案才會得一百分,我就很深地了解到我是在這樣子的環境下長大,所以我很自然的內建任何事情一定有一個標準答案。所以那時候我在Fuller讀神學的時候,我很痛苦是因為我的神學被解構了,因為你光是創造論就有不同的論述,神到底是七日呢還是幾日。對宣教也是,所謂未得之民或者你要服事誰,神的宣教的心意是什麼,我就覺得被打開眼界,原來很多事情並不只是單選題,不是只有標準的答案。
當我是用很單一的眼光,比如說我讀Fuller的期待是:我畢業之後我只要去一個國家服事當地的兒童,但當我被神打開那個眼界,原來神的宣教好大喔,原來人資也是好重要喔,原來運動也是可以真的去接觸,反而接觸到更多的人們。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台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想要去提倡的就是健身房的事工,他們說不定可以接觸到更多需要的人。當我的眼界被打開的時候,我面對的挑戰是需要有一個能夠接受多選題的眼光跟多選題那樣子的視野,這個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神的宣教是大的!察驗呼召,聆聽神的心意
董: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覺得困難在什麼地方,以及你會給卡在這當中的人什麼樣的建議,以至於我們能夠慢慢地去看到另外一種可能性。
Michelle:我覺得要先打預防針是說,你一定會被嚇到,因為就覺得你的世界本來只有一條線,現在多了好多條線,但你要相信都是神的帶領,神的手都在這些不同的線當中帶領。所謂我們講的Polycentric——不同的中心,當我們從覺得只有一個中心到多中心的時候,你的驚嚇程度是一定會有的,但同時,我覺得是需要很多的禱告跟察驗神的心意,因為多中心也表示說不定神要你走的路是其中一個,而不是另外一個。
我在宣教當中遇到了一些年輕人跟我講:「Michelle,我好像覺得只有這一條路,或是說我的旁邊的人都告訴我,只有這一條路,我回應神宣教的路之後,就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但是我會跟他們說神的宣教很大,其實祂有別的不同種的路。除了被嚇到之外,你也要能夠願意去聆聽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中心、不同人對宣教的觀點跟解釋,然後去做一些反思:原來我原本想的是這樣,但是有沒有可能有別種的可能性,或者有沒有可能其實方法有更多。比如說像我現在是做培訓,我就覺得我也是因為我的大學學位是有關於教育訓練的,所以人家在說用專業宣教的時候,我也是要用專業宣教,人家說用網路宣教,我現在目前的服事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網路上面培訓宣教士,我也是在做網路宣教。所以當你的觀點被打開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原來回應神的宣教是多選題而不是單選題。
董:你剛剛總結了三點,第一個是要做好心理預備,當我們說我們願意敞開心的時候,其實我們不一定知道我們在說什麼,當你真的敞開的時候會嚇到。我也想到那時候我2005年決定要到Fuller讀書的時候,其實我是想要學習怎麼跟不同立場觀點的人對話,我才來到Fuller神學院的,可是上了第一堂課是當時的校長Dr. Richard Mouw開的基督與文化,坦白講他那時候在分享尼泊爾的五種不同基督與文化的範例的時候,我真的第一個想法是,這應該不是五種吧,應該是四個異端加上一個正統吧,就是我會覺得在我的世界觀裡, 基督與文化的關係,就是其中一種,那其他的怎麼可以是說有可能的呢?所以第一個真的是被嚇到。
第二個當我更多地去聆聽兩千年教會的歷史,聆聽同學的觀點,聆聽不同的人的角度,我看到其實每一點從不同人的角度出發都可以是合理的,雖然我不一定同意,但是我可以理解。
第三個就是你剛剛講到反思這個階段,不管如何最終還是需要去反省反思,那我很好奇的是,最終每個人反思出來得到的結論可能不一定一樣,會不會其實真正最後的重點也不是說大家都要得到一樣的結論,而是就好像一個交響樂團裡面,演奏某一個樂器的,他的任務不是要樣樣精通,也不是要大家都接受我的樂器才是唯一的,而是我選擇了我這個樂器,我就好好地把這個樂器給演奏好。我選擇了我要這樣理解宣教,而且我這個是深思熟慮後的選擇,也是在察驗的過程當中的一個選擇,雖然這個選擇不一定是所有人的選擇,可是第一方面我不去定罪那些想法跟我不一樣的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因此就荒廢上帝放在我裡面的一個觀點,我就專心去做,而不是決定什麼都不做,可是真正的關鍵是我們也學習去愛跟接納跟欣賞和我們做出不一樣選擇的人,這方面我很好奇你的看法。
Michelle:我蠻同意董牧師講的,如果我們社會學功能論的觀點來說來看呼召,神對於我們每個人的呼召都不一樣,那當我們最終被塑造的目的要敬拜神要榮耀神的時候,就像董牧師講的這個交響樂團的比喻,當我們見主面的時候,我們都是期待我們是能夠敬拜神,我們能夠在神永恆的榮耀當中,可是我們怎麼敬拜神的方式一定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就像董牧師講的怎麼樣去愛、去包容不一樣的聲音、不一樣的敬拜的方式、不一樣回應神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加一點,我覺得這樣子的反思,這樣子的敬拜,的確還是必須在神的教堂框架下,我們在宣教上察驗我們的呼召,不能只是我們單一個體性的呼召,必須是在基督徒的信仰群體當中跟他人一起去做這樣子的反思,去互動對話而得到的察驗,然後當然是聖靈的感動而察驗的結果,不是說我自己今天覺得被呼召,要做這個我就去了,其實是一個群體性在所謂的教堂框架下面怎麼樣去回應,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宣教另一個很重要的點是「團隊」,Teamwork(團隊合作)是非常重要,團隊合作也是宣教士崩耗的前三名原因之一,這也是為什麼訓練很重要,就是訓練怎麼樣做跨文化的互動,怎麼樣跟團體互動。
我覺得參與宣教,或是我們在察驗宣教要怎麼回應的時候,真的不可以只有自己一個人,你必須要你的宣教導師,或是你的靈性指導,或是你教會的牧長、宣教機構的牧長,一起陪你走,我覺得這是比較完整的察驗過程。
從民族中心主義中得到釋放
董:這是很好的提醒,就是在群體當中的察驗以及團體合作的重要。上次我們也聊到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就是關於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這個討論也是過去兩三百年,全球主要的宣教力量是來自西方——所謂的歐美的社會——歐美的宣教士他們做了許多讓我們很感動,甚至我們今天成為基督徒,大概每個人往上追溯的話,都是因為歐美的宣教士,但是我覺得這幾十年歐美西方也開始有些反思,就是在整個宣教運動當中是不是也會有一種民族優越感,或者是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為中心,混入了我們在參與上帝的宣教工作裡面,與此同時有另外一個現象在發生,就是其實現在很多人也都認為華人教會在未來的宣教當中會扮演越來越吃重的角色,我想作為華人,我們一方面是覺得說有這個責任,另外一方面我們又如何能夠借鏡過去幾十年,西方對於這種民族優越的民族中心的反思,我們可以跟他們學好的方面,但是有一些可能需要避開我們也可以避開的呢?有些時候我也感覺到,當我們覺得華人也要接起宣教這個棒子的時候,背後好像也混雜了一些民族優越感,或者是混雜一些不一定是從福音來的自信,我也想聽聽你的看法。
Michelle:我其實還蠻感謝主,因為當我在讀Fuller的時候,我們老師很強調兩個觀念:第一個是「Check your privilege」了解你自己本身有什麼樣的優勢在你身上,就是與生俱來的優勢,或是你的身上有什麼樣的金湯匙。我舉個比例好了,比如說我出生就不用擔心有沒有水、電,我只要打開水龍頭就有水,這就是我有的金湯匙。就是如果我們用世界的觀點去看。我讀的高中是女校,所以我很早以前就被教導,女生其實有很多可以去做的事情,這樣子的觀念也是一個金湯匙,不見得每個人都會有。或是我今天神讓我有這個機會去讀Fuller神學院,這也是神賦予我而有的一個金湯匙。但我覺得在華人參與訓練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去反思,像「為台灣而教」的執行長劉安婷所講:「你要拿著你的優勢做什麼」當我們知道,我因為華人而有某一些舊有的優勢,我們可以去做什麼,而不是把它變成一個好像我們比較好的展現。
董: 因為得到的都是恩典。
Michelle:對!都是恩典,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這樣子的恩典,讓對方去發聲,那就回到第二個我在Fuller時老師一直提醒我們的,叫做「Savior complex」(救世主情結)或是「God complex」就是說當我們是有這樣子的恩典,有這樣子的優勢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會不小心就覺得我就是救世主。我今天參加這個短宣隊,對方我們要去的這個處境是非常可憐的,你看他們的小朋友都怎樣怎樣,一旦你這樣講的時候,你就會有上下之間的觀念出現了,當然這是一個現實,但在Fuller我學到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去思考,我們不能否認說,我們會有這樣子生活品質,生活條件的差異,但是我們能告訴自己,身為華人我們也可以帶上另外一個眼光:今天有這樣子的優勢跟優越,我們去到這個環境當中可以去觀察到,原來神已經在他們當中——God is already there——神已經創造了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文化跟我們華人的文化一樣,是有需要被神救贖的部分,他們的文化當中,也是有神創造出那樣非常美好的心意。所以我們去宣教是要怎麼樣去開發那些神在他們文化當中創造的美好,以至於當地的人們可以自己去發聲。
我舉個例子,這個好像很玄,我在菲律賓的巴拉旺島為我們的團隊做一個跨文化素養的培訓:Cultural Intelligence,我們的當地團隊有來自菲律賓宿霧島,有來自他們自己巴拉旺島幾個部落的同工,還有西方的一些宣教士,但是西方宣教士在那邊是少數。當我們在培訓的時候,我們就聽到當地部落的同工說,因為有這樣子的訓練,我覺得我想要更多認識我自己的文化,因為我必須要更多認識我自己的文化,我才可以知道神在我文化當中的心意,以至於我能夠去把福音傳得更好。所以當我們在回應宣教的時候,我們怎麼樣去賦權賦能給當地那些文化的處境的人們,以至於他們能夠為自己的發聲。
我覺得這比較是Fuller神學院目前在講宣教的方向,不是我們去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做,而是我們去到當中可能是因為他們缺少了一些反思的工具,就像我也是因為去了Fuller才得到這些反思的工具,可是最終的結果是他們必須要自己能夠發聲,他們必須要自己能夠回應神,經歷到神大能所帶來的轉化。
董:我用兩點來總結一下我聽到的,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去盤點數算我們所領受的禮物或恩典,我們不用否認自己的身分,我們不用否認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語言,也不用因為我們領受的恩典,就好像需要自我否定,我們需要去盤點這些;第二個很重要的是交換禮物,領受禮物要幹嘛?那是要分享的是要祝福,同時也看到我們的鄰舍我們要去的地方,那裡的人上帝也在那裡,他們也有禮物可以給我們,所以我們並不只是帶著禮物去做施捨的工作,不是這樣子的!我們去那邊我們也透過他們看到我們的貧乏,他們也透過上帝給他們的禮物,來祝福我們的貧乏;我們也透過我們所被祝福的禮物分享給他們,所以這是一個數算恩典、看見禮物跟一個交換禮物的過程,這可以幫助我們去避免這個民族優越感或民族中心主義,混雜到我們的在宣教的工作裡面。
Michelle:另外一個觀點就是說,也不只是單向而是雙向,甚至多方向的做交流,最終我們必須都是在確定我們是在回應神的愛,我們是在將神的愛傳出去。
宣教對象的轉移:邊緣性的群體
董: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其實我們一般想到宣教的時候,過去的宣教典範——兩百年前西方宣教士的典範——是很寶貴而且我覺得非常的感人,今天我們仍舊需要有人以這種典範來回應,就是可能就是買一張單程的船票然後遠渡重洋,到了一個沒有人聽過福音的地方,在那裡扎根,今天我們絕對還是需要這樣的方式,還是有這樣的地方需要有這樣的宣教士,我們的聽眾若是你的負擔,你的呼召是這個,我覺得好好地去察驗分辨,因為今天世界各地還有很多這樣的需要,但除此之外我想過去這幾十年宣教的典範也有一些新的發展,你可不可以從你的角度跟我們分享,你看到有哪一些正在發展的一些趨勢?
Michelle:我覺得除了剛才有提過的所謂的多中心宣教之外,另外就是我們宣教的對象已經比較像是我在Fuller讀到的比較多是「邊緣的群體」(people on the margin),因為我們發現在過去西方傳福音的時候,他們都是到一些比較非西方的國家或有需要的國家等等,但他們同時必須要面對人們對他們的一些看法,就是說那你們就只關注這些。以美國來講,那美國國內的需要呢?所以慢慢地整個不同世界的潮流變遷到現在,我們在講宣教的對象是針對在邊緣的群體,因為邊緣的群體就不再受只是地理位置或是族種(people group)的限制,就像董牧師講的我們在阿根廷的裡面,可能阿根廷的華人才是那些邊緣的群體。又比如說在台灣,以前我長大的時候那些所謂次文化,如動漫,那這些比較被受次文化吸引的人是不是也是需要福音;或是現在很多小孩子他們的世界就是網路的世界,那在網路的世界當中哪些人是「邊緣」,哪些人是需要福音的。我覺得這是目前的對宣教的一個趨勢:誰是邊緣群體,誰就需要福音。
董:所以就是對象我們不單單只是從地區來看,而是看到在每一個地區當中,都有一些所謂在邊緣的群體,特別是在福音上是邊緣的群體。
Michelle:另外,我看到大使命現狀報告,它提到當我們在講2050年,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住在城市裡面,那城市當中邊緣的群體是誰,我們想像的未得之民,跟2050年的未得之民那個的差距在哪裡?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慢慢去構思的。還有大使命現狀報告也提到,新的亞洲宣教的焦點第一個是全球化,再來是同國家內的跨文化宣教、散聚宣教,當然還有專業宣教跟你在你國內所謂的外籍人士的宣教,都是這個大使命現狀報告以亞洲來講, 他們研究出來新的亞洲宣教焦點。
董:很期待有一天我們也可以來談一集,就是關於這個大使命現狀報告裡面的一些精彩的內容,因為我覺得很多的資訊,其實對很多人來講是太多,一看到就覺得說不知如何閱讀,但如果可以稍微有導讀引言,其實裡面有很多寶藏是值得我們深挖的。
Michelle:像當中講整全宣教,說到年輕人目前最重要最關心的議題是有,極度的貧窮、氣候變遷、性暴力(Sexual abuse)、失業跟政治的貪腐。我就覺得很衝突,當我常常被聽到說你怎麼不是第一線,好像只有傳福音才是宣教的時候,我的衝突就是我看見我的同儕、我的非基督徒的同儕們,這些年輕人們他們注重的議題也是神的宣教啊,雖然說不是發單張的傳福音,但也是神福音彰顯的其中一環,那我們怎麼樣去對接這些年輕人,也就是他們2050年之後是我們宣教世界未來的這些年輕人,他們關注的東西,我們要怎麼樣去對接在他們關心的議題當中,我覺得這也是我這次看到這個現狀報告裡面,還蠻大的一個反思。
董:謝謝Michelle,我想最後我們談到這裡能不能用簡單的幾句話來表達:到底什麼是福音,以及福音對我們今天談的這個話題有什麼話要說。
Michelle:身為一個不到一歲就被洗禮的基督徒來講,其實很多人甚至我自己或許會以為我已經不需要救恩,因為我很早就被洗禮了所以就不需要救恩,但我因為自己生命的歷程,在家裡的背景狀況下長大之後,我發現其實耶穌的救恩所謂的福音,不只是我們永恆的盼望,也是我們現在生命的轉化,那樣子的福音不只是對永恆有幫助,而是在我們現在也能夠因為接受到神的福音,讓我們的生命從裡到外的轉化,我覺得福音的展現,對我來說就是基督的救恩與彰顯。
董:謝謝Michelle,也祝福你在培育下一代宣教士的過程當中能夠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相關資源:
1.《宣教中的上帝》,Christopher J. H. Wright
2.《深入非洲三萬里:李文斯頓傳》,張文亮
文字記錄:孔舒樺姐妹
文字編輯:呂昀嬪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