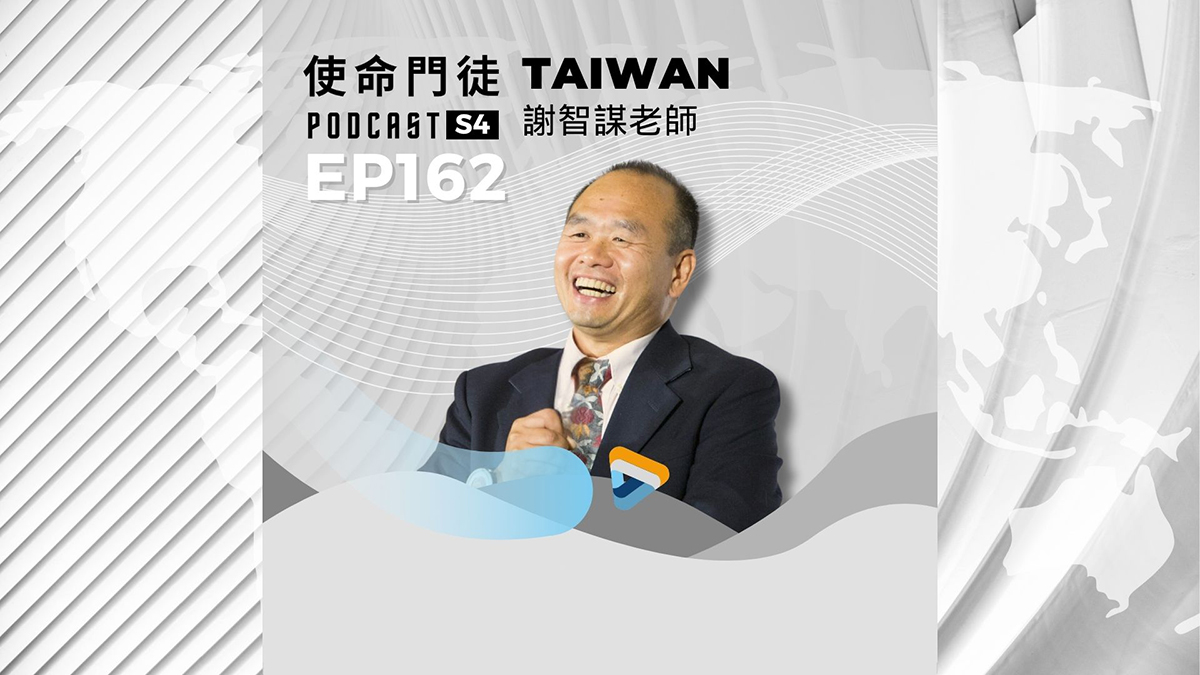
EP162 華人磐石領袖協會謝智謀老師:什麼是「多元知識觀」?如何為「青少年事工」走出一條新路?
嘉賓:謝智謀老師(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主持:董家驊牧師
董:過去十多年,華人教會越來越看重門徒訓練,也發展出各樣門訓的教材與課程,一方面這是值得慶祝的現象,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許多時候教會門訓的思維大多停留在傳授知識,與我們每日的生活實踐並沒有直接相關。今天我們邀請到有「冒險教育家」之稱的謝智謀老師一起聊聊「學習」這件事,以及對教會今日的門徒培育有何重大的意義和啟發。
我跟小謀老師是在這次錄音前的一、二週才第一次實際面對面交流,但在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見過他。那時候小謀老師在台灣帶領了許多體驗教育活動,特別是在教導青少年工作者如何做青少年事工,那時候我就是其中一位參加的學員,所以今天很高興可以和您對談。
我相信某一些領域的人對你已經很熟悉,可是對另外一些領域的人來說,可能對小謀老師還是比較陌生。可不可以請您簡單地分享自己服事的旅程,跟您走到今天一路以來的歷程?
從苦難中尋見「上帝本就給予的」
謝:我想先介紹自己是在一個家暴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在青少年時期混了幫派,接受過感化教育和保護管束,在二十幾歲時和未婚妻出國,但她後來嫁給了美國人。我1993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信主,同一時間患上憂鬱症,甚至有自殺的傾向,所以信主對我而言,使我在看待人生的價值上產生很不一樣的想法——以前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創造所擁有的,但從那一天開始,我尋找「我的有」是「上帝給我本來就有」,是原本就存有的東西。
1993年12月8日我在印第安納大學團契信主,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服事,並且很認真地查經、讀聖經,也讀了很多靈修的書,例如美國基督使者協會所出版的書籍,同時我也開始服事弟兄姐妹,我記得以前在美國時,我一個禮拜有四天都在服事。後來又當了二、三年的團契主席,直到1998年博士學位畢業便離開了美國。
我回到台灣後先是結婚,後來在一間客家教會內壢崇真堂服事,在客家地區人們信主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本身是客家人,所以在那裡服事了大概五、六年,直到內壢崇真堂獨立後,我轉往浸信會仁愛堂服事。另外,我短宣的旅程也始於仁愛堂,大約在2007至2008年間,我開始在各地做短宣的工作。
董:老師分享到1993年在美國讀書時信主,過程中,從人的角度來看,有很多不是那麼順利的事情同時發生,但卻也讓您更加認真,並參與服事。只是老師除了在堂會的事奉之外,在台灣有很多人認識您不是透過教會的事奉,而是您在教會外所做的,可不可以請老師也分享您在教會外所做的事呢?
謝:回來台灣後我就在推動體驗教育工作,因為體驗教育跟傳統的學習較為不同——體驗教育強調從經驗中學習並建構知識,所以我帶領大家從活動中建構知識並引導反思。從1998年一直到現在,台灣很多體驗教育工作、實踐、教練和行動學習事實上都跟體驗教育有很高的關聯性;另外我也在大約2002年開始,做在美國學習時的另一個主修「冒險治療」。
由於我在美國有家族治療的資格,所以當時我做了很多性侵家暴、保護管束、藥毒癮、妥瑞症和自閉症孩子的課程,大概推動了十幾年戶外荒野的冒險治療課程。當時的孩子有許多人已經走過那個過程並成為社工、心理師或老師,同時我也幫助教會做了很多的培訓,特別是為許多台灣教會做小組,團隊的培訓。
我的另外一個身分是大學的老師,從台灣體育大學到台灣師範大學大概有二十四、二十五年的時間,也在企業界做培訓,一些大型企業如高通、蘋果、台積電和聯發科……等都是我的客戶。
體驗教育不過是玩玩遊戲?反思知識的形成
董:在老師剛剛提及您所做的許多事情裡頭,其中「體驗教育」——從經驗當中建構學習,其實也正是我會認識您的原因。我知道有些人聽到體驗教育,特別是當它進入教會環境時,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只是「玩遊戲」,甚至有些教會會認為:好的教導應該是透過知識傳遞,怎麼會是玩遊戲呢?這是教會該做的事嗎?可不可以請您更多地分享什麼是體驗教育,它與我們過去傳統的教育有什麼不一樣?以及您過去是否也曾面對「體驗教育不過是玩玩遊戲」的質疑。
謝: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可以思考「到底知識是怎麼呈現的?」我們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服務業社會、資訊社會與後現代社會,其實我們很多的知識累積都是從經驗當中去建構的,因為經驗建構導致知識的累積,便會出現進一步的行動,接著再次建構知識。
我們回到聖經,從舊約到新約,包括耶穌帶著門徒那三年半你會發現祂所舉的例子,所說的風和浪,與所有門徒寫下的內容,其實是耶穌帶著門徒在實踐當中的對話;這個對話一是「耶穌自我的對話」,門徒們依照自身所見記錄下來,另一個則是「耶穌與門徒的對話」,而這就是聖經完成的過程,包括舊約也是。所以我覺得在知識論的典範當中,我們常常只強調「認知的傳遞」,卻忽略了這樣的傳遞方式對某些人來說是很困難的,比如説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kinetic Disorders, ADHD)的孩子,或是喜歡做中學的孩子,而會演變成現在這樣,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只塑造出用認知教學作為環境主體的教育模式,並非是做中實踐的教學。
教會也是如此,我們的認知、領導力、門徒訓練、牧者講道皆是以教導的方式傳授,可是從行動中實踐的卻很少,兩者是不平衡的。從我的經驗來看,假設我今天要帶領十二位學員在上山八天的過程中學習如何做一位好的領袖,第一,我會示範怎麼當一位領袖;第二,我會讓學員試著當一位領袖,並從旁觀察;第三,我會放手讓學員做領袖,並且離開。所以不管是團隊動力,不管是服事官,在這樣的方式裡我們不斷做中學,從「引導」、「對話」及「反思」去建構我們的知識體,而這即是所謂「知識的形成」。
猶如我們做質性研究,在搜集大量質性數據後將其呈現,接著後人再拿著這個數據知識做量化研究,使其最後變為量化的知識。回到信仰,我覺得在信仰中知識的傳播應該兩個部分一起做,一是聖經神學的對話引導,另一個則是經驗的傳遞、實踐和反思;我覺得兩部分建構起來,將成為基督徒經驗知識與認知知識的整體論,而如果沒有將兩者整合,基督徒會偏向一邊,成為很會講很會說,但信仰與實踐會落差,便使他人一看就覺得怪怪的。我一直認為知識的建構從經驗教育著手有助於門徒訓練,且對宣教也有很大的開展效果。
董:我沒有理解錯的話,老師談的知識是「從認知出發的學習」跟「從經驗當中的學習」並不應該被當作二元對立,必須二選一,只是過去教會似乎過度偏重認知上的學習,而忽略了其實知識的建構是在真實的經驗中發展出來的。不過,就算我們過去主要是以認知來學習,但認知本身仍舊是從經驗而來,只是我們忽略了那個部分,以至於在傳授的過程當中,我們誤以為只要把道理講通就可以了,而這麼做其實缺少了一個實踐的過程。
謝:沒錯,因為我們傳遞的大多是「間接經驗」,弟兄姐妹並沒有看到那震撼性和對話間的衝突。比如說耶穌跟撒馬利亞婦人的對話,包括把病人從屋頂上垂降下來,當你以經驗性知識看待這些經文,裡頭其實有很深且強烈的情緒認知行為觀,所以我常常覺得我們太過依賴文字符號去傳遞我們的信仰,而不用文字、符號、情緒與行為來傳遞出我們的實踐信仰。
好想改變!在實踐與反思中重整福音
董:老師,我很好奇,我們很多時候的訓練都是來自以認知為主體的訓練,所以當我們在訓練別人的時候,比如說在教會,我們要培育門徒,我們很自然地就會以「我是怎麼被教出來的方式」去教導別人,那麼今天要將一個強調認知教育為學習主體的人,開始學習從經驗當中反思,比如作為一個牧者,可能我在神學院的訓練、成長的背景都是以認知為主體的教育,可是當我今天開始看見自己這樣做的缺乏,我想要改變,不論是對我自己,或者我在帶領別人做門徒時,也開始從做中學習以經驗為主體的一種反思,這個轉換老師給那些在過往經驗中沒有太多知識是從實際經驗中積累的人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謝:我覺得我們比較大的困境是我們的認知非常的豐富,但是我們的實踐能力卻非常薄弱,我們應該在神學訓練跟教會的牧養中思考我們的實踐過程,這當中怎麼建構這個平台,並賦權我們的弟兄姐妹在這個平台裡面去實踐他在認知中聽到的。在教育現場,我們發現聽到的知識常常是會忘記的,因此我們會需要在這個過程當中鋪設一個很好的實踐平台。
比如說當我們談宣教的時候,教會就要去檢視我們有沒有建構宣教的平台,不管是差派宣教士,或是到異地或同地同文化去宣教的機制。如果這個部分教會沒有先建構,所談的宣教將永遠都只是口號。又比如我們談全球暖化,談上帝在生態中怎麼管理這個地球,當全球暖化來臨的時候,我們發現教會對全球暖化是遙遠的,我們不使用信仰觀、神觀來看我們的生態議題,所以我們講出來的東西就變成文字跟符號。
我過去曾參加過一個單位叫「為主登山」(Climbing For Christ),他們在山上傳福音、對話,甚至為人受洗,這就是一個實踐平台的例子,也讓我學到不管是傳福音、宣教或做預工,該如何在實踐當中反思並學習,我想這是台灣神學訓練缺乏的地方;實踐少反思就少,累積的知識與信仰知識系統就薄弱了,這是我覺得我們的教會神學可以去思考的部分:在實踐的過程當中,我們到底做了多少?
董:是的,我聽到兩個重點,第一是我們同時需要實踐跟反思,因為如果只有實踐沒有反思,我們只是照本宣科做以往做過的,沒有從經驗當中學習。另外一個缺失是如果只有反思沒有實踐,那麼教會的教導永遠都只會是空的,淪為口號。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很多動員性的聚會,可是結束之後卻很少有實質的行動,因為我們缺少像老師講的一個平台,讓大家有一個平台可以在當中去實踐,在實踐當中學習。
謝:是的,因為如果教會要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但我們不建構更多共同實踐合一的平台讓弟兄姐妹參與,比如說擁有木工或水電專長的會眾,他可以在木工和水電的平台當中跟上帝的信仰連結,透過他的專長實踐一個宣教模式的拓展。這些東西教會是非常陌生的系統。我們講了很多,但是弟兄姐妹回到各自的生活後所遇到的人有95%是非基督徒,而牧師則剛好相反,生活中有95%都在接觸基督徒。所以我們應該要去思考,那個實踐平台在教會牧養或神學訓練中,應該教我們的教會牧者、傳道人怎麼去建構有大量信徒的實踐平台,並且在這個平台裡,透過經驗跟對話反思,整理出以上帝為本的信仰系統的宣教跟傳福音文化。
教會要成全聖徒並建立基督的身體
董:我那天跟您聊完這一點的時候我就有很多體會,其中一個原因是我過去牧養的教會在台北市的石牌,我們教會有大量的醫護人員,在跟您聊完後我就在想:如果我再次回到教會牧會的話,其實這是一個很具體的實踐平台。因為大家都在做與醫療相關的事情,不論是前端還是後端,那麼這當中就會有很多可以反思的空間。我當時在牧養的時候,似乎沒有把握住這個機會。
今天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沒有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看過,所以可不可以也請老師給我們一、兩個例子,比如說當你講到在教會牧養現場,可以透過弟兄姐妹的專業、工作、生活建構一個實踐的平台做門徒培育,如您剛才已經有舉例的登山,還有沒有其它例子,或許帶著啟發、示範與能夠舉一反三的效果,可以幫助在牧養教會的人。
謝:我舉個例子,教會認為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成全聖徒並建立基督的身體,那聖徒是誰?聖徒就是弟兄姐妹。他們透過教會的牧養,同時這一群弟兄姐妹的「成全聖徒」就是以他本有的恩賜,在專業跟靈魂熱情所在去呈現那個聖徒的使命,然後建立基督的身體。
過去教會的牧者或傳道人總喜歡抓著聖徒的專業來成全教會的需要,那樣的信仰觀一個是以「教會為主體」,另一個是以「整個神學為主體、國度為主體」的觀念。如果今天這些弟兄姐妹的專業是水電的話,可以帶著很多非基督徒來享受上帝給他創造的水電專業靈魂,去服事,且在服事當中信仰是會顯現的。
我舉個例子,我在企業界做培訓,不管是大陸、美國、新加坡或台灣,我覺得「我是基督徒」的信仰造成我行出的一定會帶著基督徒的使命,跟基督徒那種宣教的熱情,對來參與培訓的這些執行長、財務長流露出信仰使命的生活化。回到水電專業的弟兄姐妹,他的信仰應該像這樣自然地傳遞,而不能被斷開,就像如果今天有水電專業的弟兄姐妹來到教會,我猜很多牧者都會說:「我們教會有水電、隔間或裝潢的需要,你可不可以來幫助教會?」我覺得那個信仰觀的出口跟入口是完全不一樣的。若倚靠著實踐的使命,很多運動員他有跑步的專長就可以在他跑步裡實踐信仰的對話;我們看到很多籃球員,他們在上場的時候都會禱告也會唱詩歌,結束的時候教練會帶他們禱告,我覺得那個就是美好的見證,就是信仰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覺得專業與信仰的實踐是不能切割的,特別是在傳道人跟牧者的價值觀中。當我們思考這些聖徒是在這個世界上5%、6%、7%的基督徒,在這個世界裡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美好的種子,因此傳道人跟牧者都應該想辦法成全、幫助他們。例如我們應該要去弟兄姐妹開的餐廳捧場,幫助他做得更好,而當他做得更好的時候就會榮耀神,我們便會看到上帝怎麼幫助他們。所以我覺得那個轉換的過程,從神學訓練跟教會的牧者、傳道應該把自己的信仰層面變得寬廣,而不是窄化,限縮在教會多少人、需要多少活動、要做多少事……等等的想法,那個是教會主體論,但當你以神學國度主體論思考時,你會發現信仰上帝是在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層面都榮耀祂,弟兄姐妹出去就可以展現出那個信仰的使命。
從單一思維的框架轉向「多元知識觀」
董:這讓我想到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牧師他做的一個比喻,就好像教會有兩種,一種是作為「組織」的教會,另外一種則是作為「有機體」的教會,他說任何地方只要有兩、三個人,就必然會有某種形式的組織,所以組織的教會大概是不可能完全沒有的,但是有組織的教會很重要的目的是像老師講的裝備聖徒,使教會作為一個有機體參與在信徒生命中的每一個層面,像生活、職場、家庭,以在他們所在的地方展現什麼是福音,彰顯上帝在那個領域的主權跟美與善。
我們絕對不是在說堂會組織的需要不重要,但是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堂會組織存在的終極的目的是什麼?答案應該不是為了自身的存在,而是為了上帝的國以及上帝的使命而存在。如果是從這個角度思考的話,我覺得這就像「愛」:當你真的享受一段愛的關係時,你的焦點不會只是在成全自己,讓自己被愛滿足。反而,你的焦點會是想要你愛的對方也快樂。就像教會一樣,當教會真正有生命力的時候,反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而是看到上帝放在我們身旁,那些祂所愛的世界,並且我們與上帝同心去服事上帝把我們栽在的這個處境,我覺得好像教會的生命力就會長出來,所以老師剛剛提到要從堂會為主體的這種思維方式,進入到以上帝的國為主體的這種思維方式。
老師其實也是一個實踐者,所以我相信這些您並不只是從旁觀察提出的,不是一個抽象的想法,而是在您真實地投入教會的牧養現場,培育出不論是平信徒的同工,或者牧者同工後所得的見解。那麼從老師的角度來看,牧者該如何跨出以自己的堂會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呢?
謝:在回台灣後的這二十幾年當中,陸續接觸到很多的教會牧者跟傳道人,在他們的神學訓練,和我自己也在神學院授課,我覺得我們都會有一個框架,就是我們思考上帝所運作的這個世界時,我們極度傾向用自己的那一個框架思考,而當我們用自己的框架思考時,就會在當中不斷打轉,這可能成為限制,也有可能會產生一些優勢,但是以後現代多元觀的思維來講,那是限制的,譬如說我們牧者的思考就是神學、訓練與牧養,當跨出這個範疇,其實還有很多事。在後現代的時代還有很多事情你得思考,像是國家的政治議題、政府的運作、社會社區的關係、家庭親子的關係、環境生態的關係、基督徒信仰跟靈性的關係……等等。這些後現代所關注的議題,有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的牧者對這些知識論的認知跟理解是薄弱的,而導致當要跨到教會以外的世界時,牧者是有困難的,因為當跨過去的時候你沒辦法對話。
我是一個培訓的人,當我去基督教醫院培訓的時候,我就要知道基督教醫院的樣貌,即使他有婦產科、急診科、加護病房等多個科別,但是我必須跨過去知道在基督教的世界裡面,這間醫院真正的樣貌。當我在晶片廠培訓的時候,我要知道這個產業的樣貌是怎麼樣。同樣地,現在的牧者當你要跨到不同的世界去對話,你所知道的世界就不能被框架化,特別是我們的單一框架化,這單一框架化會使我們困在裡面,然後出不去。
我記得以前我們牧者會議時一直希望台灣的基督徒能夠增加到15%,宣教士可以增加到一千五百人,這已經是十幾年前我們牧者會議時一直在提的事,可是現在我們還是在那個框架上對話、禱告,發現我們沒有實體的實踐論去跟那些世界的社區百姓,還有他們的生活觀交織出深刻的對話。我覺得我們就是無法從那個裂口(gap)出來。我做培訓的我很清楚,在校園培訓時我知道自己進入校園文化就要有校園文化的對話,可是當我進入中芯半導體培訓的時候,就有中芯半導體對話的樣貌。我是基督徒,那個以信仰為生命核心的觀念是一樣的,只是展現出來的樣貌在不同的產業的對話中就會有多元的形態。
回到教會,教會現在思考的是什麼?第一:講道分享、牧養、門徒培訓,帶領初信造就,接下來因為老年化比較嚴重,所以教會會推老人事工,又或者教會看到這個社會有需要就開課輔班,緊接著做些領導力培訓。我大概能夠猜得出我們教會裡面的框架就是這個樣子。
董:其實能做到這些就很厲害了,我明白這大概就是我們思維方式的樣子。
謝:在後現代裡面的那個「流動」,那個多元流動所蘊含的意義,在我們基督徒的信仰文化與其交織下,如何帶著那個多元流動的非基督徒跟你的世界產生很好的對話,我覺得那是在一個人的生命當中極大的接納、愛跟信仰使命,你可以有這樣的專業知識,可以走出去。這是我覺得在神學訓練裡面可以獲得更多不同的對話觀,特別在後現代的神學訓練中,那個對話觀可以把後現代裡的一些十、二十個主題都拿來跟神學生好好對話並談論這些問題。
董: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就是我們需要更多地學習換位思考,從不同人的處境來理解他們的世界長什麼樣子,我覺得一個人一生能夠做的職業大概是很有限的,所以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要去做十幾種行業,了解每一種行業的每一個框架,而是像我們聊天的時候,雖然我沒有做過您體驗教育的事情,可是在聊天當中,我試著換位思考去站在老師的角度去想您看到的世界、事情與您看待世界的方式,本身這個換位思考就是一種訓練。所以當下一次我在跟類似領域的人聊天時,我心中大概可以有一個底,以這個為基礎來繼續的擴展。
我感覺老師剛剛是否就是在鼓勵其實不論是牧者,或者某一個領域的專業人士,我們其實都需要有不同的眼光跟框架來理解周遭的環境,而這本身是一種素養,一種訓練的過程,我這樣理解正確嗎?還是老師要補充。
謝:我可以補充,因為基本上你對多元知識觀是開放的,當你對多元知識觀是開放的時候你就比較可以換位思考,並同理跟你不一樣工作的人的思考方式、歷程跟他的觀點,或是他說出的語言。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對多元知識論報以開放性的特質,所以我們會期待在神學訓練中,不管邏輯系統或多元知識觀,這些東西都要放在我們的教會當中,讓我們可以擁有多元知識觀、同理與換位思考的能力。這些能力我覺得在本質上是比較重要的,因為在我們的神學訓練中不見得就有教這種同理、換位思考或者是多元知識觀的理解跟接納。
董:老師可以再多解釋一下你說的所謂「多元知識觀」是什麼意思嗎?
謝:我舉個例子,當我們聽到佛教徒跟我們講佛教的世界時,我會去理解他的表達、他的思想、他的歷程、他的想法,我也可以提出我的理解、提問,然後再一次去理解他的想法跟他的知識現象。我不急著去反駁他的信仰,不管是衝突論或者是對立論的內容,我覺得那個理解就是我所說的多元知識觀。又或者,我可以理解一位基督教醫院的醫生和我談他工作中的衝突,不同科別間對話的衝突;我理解與接納這個樣貌,但我不會想要去嘗試要說服跟改變。
我覺得這個多元知識觀是在後現代裡人應該要有的,因為你有這樣的知識開放度的時候,對於不同人的想法跟知識你比較容易去理解,也會想到他的歷程,能夠跟他對話、引導,同時因著多元觀的理解,你就會去接納一個人。我覺得那個接納的核心就是耶穌生命的核心,也是我們一直缺乏的多元知識觀的對話。就像我以前在博士班有一堂課叫argument(爭論)跟negotiation(談判),我們花了三週在談兩者的異同:我有沒有辦法對多元知識的東西有更多的開放、理解、想像跟歷程的對話?如果我們的教會跟神學傳道人在神學訓練上都能夠有這種知識論的對話時,我相信福音工作其實困難度沒有我們想像的大。另外,就我二十幾年來的經驗,人其實在引導反思的時候很容易與信仰相遇。
「多元」等同「否定真理」?「後現代」就是「敵基督」?
董:我想每個人在聽到「多元」或「後現代」的時候感受可能都不大一樣,對一些人來講,這可能是一個很正面的字眼,但對另外一些人來講,這可能是洪水猛獸,甚至一講到「後現代」,可能就會講到這是不是「敵基督」的文化,講到「多元」,是不是就是反對和否定有絕對真理!我覺得可能是一種底層的抗拒,為什麼那麼多的基督徒我們很難有多元知識觀?是因為我們的底層可能就抗拒了多元和後現代,或者是直接把多元跟後現代等同於負面、反信仰,不知道老師有沒有面對過這樣的質疑?您會怎麼樣去跟這樣的一群人來分享。
謝:我覺得基督的核心就是我們的信仰跟上帝的連結,若你沒有非常深的信仰,很多福音工作都只是假象。若上帝的使命在你裡面,你會很清楚既然這個世代用多元的方式呈現。
以性別議題為例,當有不同性別議題的考量出現在我面前時,我需要跟他對話的是他的思想、他的世界和他目前的想法,甚至困境、他所面對的問題等等。我喜歡聽到這樣的對話,然後我提出這樣對話的觀念,這代表一件事情是「我不用把他當作我討厭的人,然後就不跟他對話」,而是「我覺得我想要親近這個人,我想要理解、接納這個人」。我覺得這樣的接納不代表他跟我之間就會怎麼樣,而是我很清楚知道這件事情會放在我生命當中;我怎麼樣將他和他的需要放在我的禱告當中,我也可以為他禱告,而禱告的時候就是信仰出現的時候。
我過去在體大教書時,我有很多學生也有這樣的議題,但是有一些學生後來也信主了。我不覺得這種多元的呈現只出現在這個世代,但是我們怎麼用開放的方式去接納這種多元觀,這代表我們信仰中準備的那個容量夠不夠大;如果我們的容量不夠大,那些反信仰的模式進到我們裡面的時候,我們就想去反抗、對抗、敵對或不理它,這樣反而無法成就基督的容量。但在接納對方以後,他會感覺他是被愛、被恩典、被救贖的,有人和我一起面對這個問題,所以這二十幾年來我覺得信仰的那個核心一定要守住。
董:是,我覺得這有回答到我的問題,就是不論是多元知識觀、同理心或養成一個換位思考的習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能,但對於一個基督徒而言,我們之所以能夠帶著我們的信仰去做,我們所做的事情有一個完全的整合,其實它的關鍵就是我們與基督的連結,而當這個連結是真實且深刻的時候,我們的愛就不再出於懼怕,接觸到的東西不會反過來玷污我們。
就好像當耶穌在觸碰醫治病人的時候,他並沒有因為病人的病就不去接觸他們,反而伸手醫治。可是一個很明顯的對立面就是法利賽人,當然他們可能也是本著摩西的律法,以及自己害怕染病,好像我們都很害怕,幫自己設了很多的界線,怕跟這些人有任何關聯。可是我們看到耶穌展現出來的是一種當他在父裡面有一個深深的連結,當他自己活在父子聖靈在三一上帝關係當中的時候,他不用害怕被汙穢給玷污,反而是透過接觸去醫治。
所以剛好老師您說到,也許表面上當我們覺得自己是為了捍衛信仰而反對多元知識觀,好像是一種信心的表現,可是有沒有可能這是因為有些人覺得還是要保持一些空間,或者有沒有可能有些時候我們只是過度堅持自己的想法。這其實是一種因著對自己所信的不信任,所以感到害怕,我們很害怕一下就被牽走,一下被帶走了。
謝:我舉個例子,有些人坐高鐵時旁邊來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他就很緊張、很害怕,我常常去尼泊爾爬山,那裡很多的山屋都會掛很多其它宗教的相片,但我還是睡得很好,為什麼?因為你是自由的,在你跟上帝的連結中你是自由的。所以包括我去穆斯林地區,我是自由的,所以我覺得信仰的核心點如果抓住的話,你就可以自由地活在非基督徒當中,然後成為生命的見證去愛、理解和接納,甚至在適當的機會傳福音給他,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介入方式。
可是當你切斷了這些對話的時候,你會被排擠,這也是我會期待台灣的基督徒能夠在這個廣大的層面當中學習的;我常常覺得我只要一個禱告,就是為一群人五年禱告,他五年只要帶一個人信主,我們基督徒就有10%或12%了。如果台灣每一個人都帶一個人信主,那基督徒的增長是可觀的。但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出在我們的信仰在生活中實踐的實踐論、多元知識觀的容量跟對於後現代的理解、同理跟換位思考的容量不夠大的時候,我們就會切斷那一個可以在世界裡面,在生活裡面去作見證的機會。
董:這就好像是耶穌為門徒的禱告——在世界,卻不屬這個世界。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卻反過來變成「我們不在這個世界,卻屬這個世界」。就是我們跟世界是脫離的,可是我們很多的思維價值觀跟這個世界卻沒什麼兩樣,我必須很誠實地說,我覺得這是今天教會所面對很大的危機。
謝:或是我們裝作兩樣。
牧養青少年要進入他們關注的世界
董:就是真正的危機或許不是這個世界的世俗化威脅到教會,真正的危機或許是教會自己的世俗化,而我們其實在無形當中已經接受了這個世界成功的定義,什麼是美與善的定義,但是我們卻又跟世界做切割,以至於我們又不在世界當中。
關於「後現代」的部分,記得老師在上一次的聊天中提到,其實今天的年輕人與青少年就是沉浸在這個後現代文化的處境當中,而今天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大概我沒有聽到哪一個地方的華人教會說「我們的青少年事工做得很好」,我聽到的都是「我們的青少年正在離開當中」。當然其中有很多理由,我們可以說因為整體社會的老化,或是青少年畢業之後離開家鄉去外面工作,不一定是教會自己的問題,但是從結果來看,各地的華人教會似乎都在青少年工作的困境與年輕人的離開中掙扎。不知道老師對於青少年事工所處的這個處境以及他們選擇離開,以您的角度有什麼可以給教會的建議?
謝:第一,我們先思考在台灣神學院目前教青少年牧養的其實很少,代表我們神學對青少年牧養的研究,或是那個系統其實是薄弱的,這是第一個我覺得要提出來反思的部分。我們在這個時代裡面對青少年,特別從兒童轉變為青少年的那個過程當中,很多的變化包括他們生理上的改變,信仰該如何面對那個衝擊?跟他們進入社會面對後現代知識上的衝擊時,這些基督徒又該如何面對?
第二個是這些孩子在教會裡面服事的樣貌。我舉個例子來講,他們通常就是聚會、查經或者一個心靈小語,然後聖經心靈小語讀完了就問有沒有誰需要代禱,然後結束聚會。有的教會會帶他們去溯溪、去打漆彈,大概青少年牧養就是這樣。這是主流文化所造成的,認為聚會就應該大家圍在一起,做禱告,然後為彼此生活代禱。我們要思考青少年所面對的世界,包含感情的議題、人際關係的議題、功課的議題、親子的議題、自我成長、自我肯定或自我學習的議題,與面對自我信心、自我概念的這些東西,面對很多他們不知道要怎麼辦的世界,面對他們的生涯、他們會碰到什麼事情。我覺得青少年在複雜的學習當中是很困難的,可是當他們來到教會的時候,教會運作的模式是讀聖經、唱詩歌,然後問:「有沒有代禱事項?」或許答案會是「我媽媽身體不好」那我們的牧養就結束了!沒有回到他們的世界裡面,他們怎麼看自己的生涯?他們怎麼看上帝給自己的熱情跟靈魂的所在?他們怎麼看專業的選擇?怎麼看跟父母親的關係?怎麼看他跟學校、社會、社區的關係?我覺得這些東西在後現代裡面是複雜而龐大的,這對我們教會,特別是牧養這些青少年的傳道人比較多又偏偏回到「教會主體觀」,忘記以「國度主體觀」處理這些青少年所面對的生命衝突,或者是他要選擇什麼樣的一條路走,走他未來的方向等等。
如果換作是我來牧養,我應該要讓青少年去理解這些東西,所以假設我今天想要理解這個全球暖化的問題,我會在教會為青少年辦一個全球暖化的講座,讓青少年的知識觀變得寬闊且不會進入教會那個唯一的框架之中;他的框架可以透過這樣的平台被打開。如果我要談108課綱核心素養,或是未來的118素養,我應該請很多很棒的老師來讓這些青少年了解108素養跟118素養談到的問題,談到的歷程導向的重擔。在現在教學裡面孩子面對很多的問題,他們要參加很多的活動,那他們怎麼找到一條路,而這些議題都是教會可以用實踐平台讓青少年找到或發現的;教會給他們更多知識論的一些想法,教會也鋪設一些實踐平台,例如我們華人磐石領袖協會就鋪設很多的實踐平台,讓一年一百、兩百個孩子到海外去服務、去宣教,我覺得這是重新看待自己信仰或自己的生命怎麼在這些實踐平台裡,跟知識論共同建構、架構出一個比較完整健康的青少年的一種樣貌。
「牧養」真的只是牧者的事嗎?
董:謝謝老師,您剛剛講到一點我覺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們的青少年牧養是不是進到他們的世界,進到他們所在面對的,不論是家庭、未來或者是他們眼前所看到今天這個世界在面對的各樣挑戰,如氣候變遷、暖化、全球地緣政治帶來的不穩定性。
謝:和正義觀等等。
董:包括像各地都在做的教育改革,像剛剛老師提到的108課綱是台灣這幾年在做的一個教育改革,一個典範的轉變。當然有些時候大家也會覺得一頭霧水,好像只是換了一個名稱,不明白它其中的內涵到底是什麼,但是老師剛剛就提到說其實這些不了解,都是今天教會進到學生孩子生活當中的一些切入點;也許這些東西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但不代表教會的身體,就是基督的身體當中沒有人曉得。
我們不知道但就如同老師上次跟我說的:牧者不見得一個人知道所有的事情,但牧者能不能成為一個資源的平台?去找到懂的、明白的人,然後甚至跟這些人一起走一段信仰整合的路,就是也許那位專業的基督徒他本身的專業很強,可是他沒有想過自己的專業跟信仰有什麼關係,而牧者可能很在意一個人的信仰,可是可能也沒有想過信仰跟弟兄姐妹專業的關係;弟兄姐妹的專業加上牧者在乎的信仰,這種資源的共走一哩路,在這種共創平台本身它可以就先發生在牧者跟不同行業的弟兄姐妹之間。
當牧者本身連接到這些人之後,一個議題浮現的時候,牧者也可以曉得面對我所牧養的這一群人,他們在面對這個議題有哪一些的人是可以一起找來談的。我覺得這個很寶貴的想法,就是說在所有牧養跟裝備的重擔上,雖然牧者非常重要,但它從來不應該是落在一個人的身上,而是整個教會的身體彼此牧養,上帝給基督徒、給教會的恩賜是很豐富跟多元的。
謝:是的,我覺得這個共情、共學、共創的過程是一個非常美麗的過程,但是特別是牧者或傳道人應該更懂得利用資源連結,整合基督徒弟兄姐妹本有的知識跟專業,以及他信仰觀的實踐能夠對更多弟兄姐妹或更多非基督徒產生影響力。我相信教會提供其需要上的滿足也是非基督徒會想要來教會的原因。
連結資源以「以社區為主體」開展宣教工作
董:老師除了在做這些青少年培訓、企業培訓和教會小組長訓練之外,其實您也透過自身的專業在做許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一般想到跨文化宣教,其實我們有一些固定的公式,就像老師剛才講到教會想到青少年牧養的時候有一些固定的公式,那這些公式不是不好,它之所以會成為公式一定代表在某些處境、某一個年代或某一個時空下它是很有用的,但是可能是現今時代的變遷過快,或者各地的處境都不太一樣,所以老師也不斷在摸索,找到一些不同的宣教實踐方式,這部分可不可以請老師也分享一下,在宣教的策略上您是怎麼做的?
謝:在2012年以前,我的宣教策略就是跟教會一起出去,2012年以後,我成立了華人磐石領袖協會,開始帶著一群同工一起出去。剛開始,我們跟浸信會的曾敬恩牧師去支援尼泊爾照亮生命英語學校(Lightening the Life English School),那間學校的中間剛好有一間浸信會教會,那時我就開始去支持以社區轉化為主體的宣教工作,以社區轉化經濟、教育和信仰,而不是以教會為主體的社區改變工作,我覺得兩者的核心點是不一樣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也帶著當地的老師做思維、做想法改變,然後當然基督徒人數也越來越增加。而該所學校在尼泊爾的教育排名也從原本是倒數2%到現在是72%,所以教育也改善了。另外,以經濟為思維的工作我們現在還在運作社區經濟發展的一些想法,我們養了豬、種了咖啡等等作物。
後來我又去了印度,我知道我這樣的臉孔在印度做宣教大概很快就沒了,所以我怎麼樣能夠支持當地的牧者在他能夠接觸的範圍做宣教工作。我從一個四萬人的貧民窟開始建立教育中心,我們教了一百多個孩子英文,因著這個中心,我們的牧者就可以接觸貧民窟的家長,後來那些家長也信主了,因為這樣子我們在那個貧民窟就建立了三間教會。
後來我們又蓋了一間美容學校訓練貧民窟的媽媽可以做美容,藉此找到工作,而那位牧者則透過我們的支持系統開始做福音工作,他現在在印度開展了十八間教會。
我們也從台灣派宣教士前去泰北,但後來因為各樣的因素,特別是身體的因素就回來了。我們最近也在禱告看有沒有牧者要過去,我們要在泰北建立中文教會。我們有一百五十個孩子在學中文,一百五十個中文學生乘以兩位家長,再加兄弟姐妹,那個地區我們牧養的人數可能有到五百個人。
那個以信仰為核心的概念永遠會存在,可是以教育為主軸,我怎麼幫助教育?而以社區為主軸部分那邊有咖啡,我如何用咖啡來賺取利潤,以支持教育跟信仰?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以社區為思維的主體,加上寒、暑假帶著台灣的年輕人去那邊服事,在看到很多的不一樣以後,他們在台灣繼續為當地去募款,或去想一些方法在自己的社區做社區的協助跟轉化的志工,我覺得這是一個多元的藍海策略的思維。
我知道我自己在尼泊爾宣教會有很大的困境,而在印度,我覺得我要進入社區其實是不容易的,我知道很多的宣教士都是非常不容易才進入那裡,但是我自己思考到我的專業是將教育、信仰、社區跟經濟結合,因此我就用上帝呼召我的路去做。磐石在那裡從2012年到現在做了快十二年,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個實踐的宣教策略其實很適合我們在跨文化宣教當中——找另外的路來做不同宣教的模式。也特別謝謝東海靈糧堂開始有很大力地支持我們的整個福音跟宣教行動,還有門徒訓練、牧者訓練的課程;因為我的有限是我在神學訓練的有限,所以剛好也找到牧者能夠支持我,我很感恩覺得一個使徒加上牧者,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對接、對聯的過程。
董:我其實蠻感動的,特別是講到互相的搭配,小謀老師您在做的這些事情可能不是一個牧養教會的牧者會去想到或者熟悉的,但是小謀老師您也意識到自己有的強項優勢可以發揮,但是也有自己需要補足搭配的地方,我覺得如果我們在宣教的這個場域,每個人都存有這樣的心態,其實我們能夠做的事情一定比現在遠遠多得太多;今天很大的一個困難就是我們很難跟彼此合作,我們每個人就是看著自己有的,看不起別人有的,然後我們就努力做自己的,但是很多的資源、網絡和合作的機會就這樣白白錯過了。
可是我想宣教、建立教會和培育門徒的方式有很多種,坦白講我們也應該沒有唯一正確的一種方式,而既然它沒有唯一一種正確的方式,我覺得也許每個人都會有每個人自己的恩賜,讓他更傾向於某些方式。但如果我們同時能夠用老師剛講的多元知識觀看到自己的框架,分析自己的優點是什麼?潛在的缺點是什麼?並且更主動地去找到能夠跟我們互補合作的夥伴。我覺得其實無論是在本地教會建造,或者是遠方的跨文化宣教工作,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會發生。
謝:是的,我覺得在服事的這個過程當中,我自己有很多的不足,雖然我是在教育系統裡面服事,教學這麼多年也樂在其中,但是我覺得在宣教工作裡面你要承認自己非常的有限,在當地的軍事、政府、經濟以及社會的困境當中,我的神學怎麼樣找到適合的人協助我?我在社區轉化裡面有沒有更適合我的人幫助我訓練當地的社區長老、牧者或居民,我覺得在這一些主軸裡面,對我而言我需要更多的策略、資源的連結,把更多人在這個上帝的平台當中合一,完成上帝所喜悅的事情。我覺得作為一個基督徒你要很清楚知道是這個平台建構完,上帝就在裡面做祂自己美好的事情,你要讓人進來,讓更多人進來,你就會看到美善在裡面更好的存在。
多元知識觀與共行、共創、共學精神的實踐
董:老師,最後兩個問題,倒數第二個就是我們今天聊了很多,如果今天面對一群華人教會的牧者,或者不見得是牧者,有的時候也是在不同各行各業愛主的弟兄姐妹,從您的觀察您會給今天的華人教會一、二個覺得是很重要的提醒跟建議?
謝: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當我們訓練門徒,不是讓他只有在教會服事,我們還要讓他跟上帝有很深的連結,能夠在生活當中去見證基督的信仰,也成為在這個世界中另外一種宣教的模式可能被建構出來。所以他要有更大的知識觀的接納度,他要有更多跨文化社會同理,並用這種同理心的樣貌在這個宣教文化裡去接納更多元的存在,這是我對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傳道更深的期待。
接下來這個社會一定會有非常大的變化,特別是AI,那我們能不能在這樣的時代當中擁有多元知識觀,能夠更龐大地去容納這些東西,透過上帝來改變,跟這個時代共行、共學、共創。這是我希望我們一起來思考的問題,而傳統的知識模式可能要有更多實踐平台跟資源連結的方式,讓它有不一樣的出現樣貌。
董:謝謝老師,老師不斷強調有三個重點,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思維方式需要能夠更新。第二個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實踐的平台,而不只是停留在思維方式。第三個就是我們不但是跟彼此,也跟上帝放置我們的這個世代有一個共行、共學、共創的精神。老師最後我想說能不能請您用簡單幾句話來表達,對您來說耶穌基督的福音是什麼?以及福音對我們今天所談論的這一切有什麼關聯?
謝:我覺得福音對我而言是一個恩典的救贖,是一個無條件的接納跟愛。因為當我在我的靈魂當中時時刻刻體會到這個恩典的救贖,跟無限的接納和愛的時候,我覺得那個力量是從上帝裡面來的,所以他的熱情跟靈魂跟呼召會從那裡面生出來,而不是我自己去找一個。當我生出那個東西來的時候,傳遞出去的語言就是帶著福音信仰、信念的語言。
師大所有的老師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很多認識我的學生也知道我是基督徒,因為我從來不遮蓋我基督徒的這個名字。我就是基督徒跟我是謝智謀一樣,我覺得這件事情如果讓大家看到,我們的信仰是怎麼在生活當中實踐,這就是我們傳遞福音非常好的一個實踐模式。
董:是的,謝謝老師今天的分享,不論是對我們這個認知框架的挑戰,或者是鼓勵我們有一個實踐的平台,或者是共行、共學、共創精神的提醒,我覺得都是今天我們很需要的。
如果你聽完這一集,我也鼓勵你可以想一想,上帝把你安置在這個地方,當你不再以自己為中心,以自己的組織機構堂會為中心,而是看到上帝呼召我們要服事的這個群體的時候,那有誰是我們可以主動去學習的?有誰是我們可以主動去尋找探索可能的共行、共學、共創的機會?謝謝小謀老師。
相關資源:
文字記錄:高昕正弟兄
文字編輯:呂昀嬪姐妹






